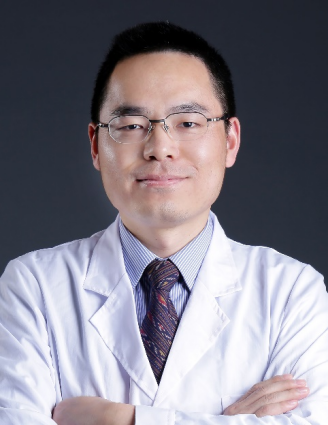三阴性乳腺癌(TNBC)是一种极具异质性和侵袭性的乳腺癌表型,其化疗耐药性或放疗抵抗与肿瘤微环境、膜蛋白(转运蛋白)的过表达、表观遗传变化以及与肿瘤干细胞(CSCs)形成相关的细胞信号通路/基因的改变相关[1]。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IF = 12.822)发表TNBC相关综述[2],分析了TNBC化疗耐药及放疗抵抗的因素、CSCs的作用、TNBC的治疗策略及TNBC治疗的最新进展等内容。【肿瘤资讯】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TNBC进展、化疗耐药、放疗抵抗及其逆转的生物学标志
TNBC可分为6种亚型:基底细胞样1(BL1)、基底细胞样2(BL2)、管腔雄激素受体 (LAR)、间充质干细胞样(MSL)、间充质样(M)和免疫调节(IM)。所有这些亚型均与上皮-间充质转化(EMT)直接相关,除产生耐药性外,EMT还参与肿瘤发生及不良预后[3]。
肿瘤微环境
肿瘤微环境 (TME) 在TNBC发生、进展、增殖、免疫抑制、血管生成、侵袭/细胞迁移和不良预后中发挥重要作用。TME由参与多种信号通路调节的各种细胞组成,这些具有不同表型特征的细胞群使得TME更加复杂。TME主要通过内皮系统和免疫细胞在肿瘤细胞和周围组织之间形成微环境,负责CSCs发生的EMT也可能由复杂的TME诱导。因此,了解TME的复杂性或将为制定精确治疗策略提供重要参考。
膜蛋白(转运蛋白)的过表达
跨膜蛋白在生物分子进出细胞的转运过程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主要参与细胞自噬、肌肉收缩、表皮角化和免疫反应等几种生理功能。多项研究表明,跨膜蛋白在癌症中受到不同调节,并参与肿瘤发生和耐药性产生[4]。TNBC固有或获得性化疗耐药是由药物外排 ATP 结合盒(ABC)转运蛋白家族的许多成员过表达引起的。
ABC 转运蛋白
ABC转运蛋白分为七个亚家族(A-G),由48种蛋白质组成。ABC转运蛋白需要ATP通过细胞膜运输物质。由于ABC转运蛋白的过表达,细胞外排机制增强,导致多药耐药性(MDR)的发展[5]。
研究人员试图通过两种靶向ABC转运蛋白以克服化疗耐药:a)抑制ABC蛋白的活性和 b)抑制ABC基因表达。ABC转运蛋白活性抑制剂,如氨氯地平、环孢素、维拉帕米、硝苯地平、奎宁和dexniguldipine,与化疗药物联合使用,以确保耐药逆转[6]。PZ-39抑制剂降低了ABCG2活性并促进了ABCG2蛋白的降解。几项用于治疗TNBC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探索ABC转运蛋白抑制剂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联合使用,如EGFR、FGFR、VEGFR、PI3K/AKT和其他化疗药物[7]。
TNBC放疗抵抗及其逆转
TNBC初期可通过放疗获益,但晚期和转移性TNBC可能会对放疗产生抵抗。放疗抵抗相关机制目前尚不明确,脂肪酸合成和氧化增加与乳腺癌放疗抵抗相关。最近的研究发现,乳腺循环肿瘤细胞 (CTC) 向辐射损伤区域迁移是癌症复发的促成因素[8]。导致肿瘤患者放疗失败和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放疗抵抗。放疗抵抗也可由代谢(尤其是糖酵解代谢)的改变导致。放疗患者的代谢途径显示其调节自噬、溶酶体降解和线粒体活动的基因表达增加,以及对线粒体呼吸的显著依赖性和对 Warburg 效应(葡萄糖摄取和代谢的加速)的依赖性降低[9]。
目前有一些研究探索了转移性TNBC治疗中发生放疗抵抗的几种分子机制。研究显示,与转录机制相关的 NF-κB激活和一系列抗凋亡基因激活、清除损伤性自由基和抑制促凋亡基因导致肿瘤分子现象变化,从而改变了其对放疗辐射的反应[10]。在另一项研究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增强了放疗抵抗 MDA-MB-231 细胞赖氨酰氧化酶的释放。Bai 等人发表的报告证明 eIF2α磷酸化激活ATF4,从而导致谷胱甘肽生物合成和细胞内 ROS增强,TNBC出现抗辐射表型[11]。据另一项研究报道,调控转录、RNA剪接、延伸和输出的THOC复合体的过表达是 TNBC产生放疗抵抗的原因,在放疗抵抗TNBC小鼠模型中,阻断THOC活性可以增强治疗反应[12]。
CSCs
CSCs参与肿瘤发生、异生、复发和转移。大多数细胞增殖可通过有效的治疗消除,但 CSCs可能持续存在并易于复发,因为其具有侵袭性和化疗耐药性[13]。因此,了解CSCs特性对于通过靶向CSCs迎来癌症治疗的新纪元而言至关重要。目前对CSC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来源、细胞表面标志物、肿瘤增殖机制、复发和消除CSCs的治疗策略[14]。细胞表面标记物如分化簇 (CD)20、CD44、CD90、CD133、CD200、乙醛脱氢酶 (ALDH)、上皮细胞膜粘附 (EpCAM)、THY1和ATP结合盒成员 B5(ABCB5) 在CSC群体中过度表达,这些标记物可以用来区分实体瘤中其他细胞群的CSCs 。Jain等最近的综述详细讨论了CSCs发生和根除的机制[15]。
CSCs 细胞信号传导和化疗耐药性发展
细胞信号转导与TNBC中CSCs的发育、自我更新和分化有关。具体而言,Notch、Wnt、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 和hedgehog(Hh)通路在发生CSC相关化疗耐药时上调;其他由受体酪氨酸激酶 (EGFR、VEGF)、非受体酪氨酸激酶(PI3K/AKT/mTOR和RES)和其他转录调节因子(nanog、YAP/TAZ和OCT4)介导的共同通路,在增殖的CSCs中过表达。这些通路在肿瘤复发中起关键作用,所以控制TNBC 复发的可能方法之一是破坏上述细胞信号通路。因此,通过TGF-β、Notch、Wnt/连环蛋白和 Hh 信号级联等通路来抑制CSCs增殖,可能有助于完全根除肿瘤复发(表1)。
表1 化疗耐药的信号通路和相关CSC标志物以及用于逆转化疗耐药的抑制剂
表观遗传失调
靶向基因表达和功能的改变以及基因突变可导致DNA损伤,从而导致细胞凋亡失败。因此,肿瘤发生过程中细胞基因组的表观遗传学变化在化疗耐药中发挥关键作用。甲基转移酶可以通过抑制转录因子蛋白修饰 DNA 甲基化参与恶变。这些蛋白对于转录过程中甲基化半胱氨酸的结合至关重要。此外,组蛋白H3和H4的组蛋白乙酰化和组蛋白甲基化修饰参与了基于表观遗传学的化疗耐药过程。DNA甲基转移酶 (DMT) 的过表达提高了甲基化半胱氨酸的水平,从而促进了乳腺癌早期的转录过程。同样,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HMT)、组蛋白乙酰转移酶 (HAT) 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DAC) 的异常表达可诱导 DNA 损伤,并导致预后不良和化疗耐药。
TNBC治疗策略
细胞信号通路介导的药物递送
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通路
PARP在许多生物活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DNA修复、基因组维持和细胞凋亡。PARPs已被证明是抗癌治疗的一个很有前景的靶点,因此,现阶段PARP抑制剂(PARPi)被认为是TNBC的前沿治疗方法。PARPi主要靶向PARP1,后者负责识别单链DNA断裂。许多PARPis,如奥拉帕利(olaparib)、rucaparib、iparib、veliparib、talazoparib、尼拉帕利(niraparib)和geparixto,已作为单药治疗和/或与其他化疗药物联合治疗进行了临床研究。在针对TNBC患者进行的奥拉帕利Ⅰ 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1/9例携带BRCA2突变的BC患者在使用抑制剂后长达60个月获得完全缓解,3/9例携带 BRCA2 突变的患者为4个月的疾病稳定[16]。
表观遗传靶标介导的药物递送
针对肿瘤的表观遗传靶标阻止细胞侵袭的新疗法是基于在不改变一级序列的情况下调控基因表达的原理。组蛋白乙酰化和DNA甲基化的异常表观遗传学变化可能促进肿瘤发生和化疗耐药性发展。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DAC) 抑制剂可用于抑制组蛋白中赖氨酸残基的异常乙酰化,从而中断染色质形成启动基因转录。所以HDAC抑制剂可导致同源重组蛋白耗竭并阻止DNA损伤修复,从而诱导BRCAness并使TNBC细胞对PARPi敏感。当 HDAC 抑制剂与顺铂或 PARPi 联合使用时,有研究结果表明TNBC细胞的活力降低[17]。
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是TNBC治疗的一种新兴方法。已发表的文章表明,TNBC中全基因组 DNA 甲基化的模式不同于激素阳性BC [18]。Kang等人报告称,DNA甲基转移酶 STAT3-DNMT1在肿瘤抑制基因的启动子位置发生去甲基化,并导致PDZ和 LIM 结构域蛋白 4(PDLIM4) 以及 von Hippel-Lindau 肿瘤抑制 (VHL) 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转移[19]。Hsp90是一种分子伴侣,可引起各种蛋白的成熟,如AKT和PI3K。因此,抑制Hsp90 可能通过抑制与肿瘤生长和转移相关的信号级联反应,从而带来潜在的治疗益处。
其中一项研究证明,在携带4个 T1 细胞的 TNBC 小鼠模型中,Hsp9抑制剂 ganetespib 降低了 MDA-MB-231 细胞的活力,抑制了肺转移。Ganetespib 还可增强 DOX-环磷酰胺在 TNBC 异种移植物中的作用,并与 PTX 和 DTX 联合诱导有丝分裂障碍和细胞凋亡作用。此外,有Ⅱ期临床研究评价了ganetespib作用,结果显示TNBC 患者6个月的临床获益率 (CBR) 为9%,中位 PFS 为7周,总生存期为46周[20]。
受体介导的药物递送
与乳腺癌/TNBC相关的异质性归因于各种细胞表面受体的过表达。通过使用这些细胞表面受体的配体/mAb或拮抗剂,可以控制这些受体的细胞结合,并且可以通过mAb/配体偶联的NPs实现药物靶向作用。数项研究已证明,通过受体介导的药物递送可增强靶向疗效和药物效力。
免疫疗法
细胞中免疫系统的激活受肿瘤相关抗原 (TAA) 调节,TAA可导致组织(包括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的炎症。TAA 可以通过趋化因子和白细胞介素增强肿瘤中CD8+ T淋巴细胞的表达。在免疫过程中,转化的恶性肿瘤细胞可以被自然杀伤细胞(T细胞、IL-6等)消除,但该过程在肿瘤细胞中会出现异质性,从而产生耐药性。这种适应性耐药可能是通过抗原丢失、细胞信号级联失调和/或T细胞刺激延长获得的,耐药将导致细胞因子表达丢失,从而导致免疫效应丧失。
免疫效应缺失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 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 (PD-L1) 蛋白过表达高度相关。PD1和PD-L1过表达可诱导异常信号级联反应,并诱导CD8+ T细胞衰竭,从而使肿瘤细胞逃避T细胞免疫攻击,直接影响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及临床预后。
TNBC治疗最新进展
三阴性乳腺癌 TNBC CAR-T 细胞治疗干预的最新进展
实体瘤的CAR-T 疗法与其他治疗形式联合使用时,可以获得更好的临床结果。例如,可以使用ECM-或CAF-靶向药物来增强CAR-T细胞的抗癌作用。抗血管生成药物可用于改善 CAR-Ts 向肿瘤部位的运输,巨噬细胞或单核细胞清除药物有助于增强CAR-Ts的抗肿瘤作用。对此,gdCAR-Ts 和表达CAR的NK细胞 (CAR-NKs) 已被用于研究治疗包括 TNBC 在内的血液和实体瘤。这些不同的CAR表达效应细胞可能有助于克服各种 CAR-T治疗困难。总体而言,通过选择最适合的靶抗原和解决未满足的限制来增强实体瘤中CAR-T治疗的特异性、安全性和疗效,对于TNBC中CAR-T治疗成功至关重要。
肠道菌群 (GM) 在TNBC中的作用及其治疗
在过去几年中,免疫治疗在TNBC和其他癌症中的应用有所增加。既往研究均表明,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CI) 治疗 TNBC 可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获益。癌症和抗癌治疗与 GM 有直接的相互作用,应用药物微生物制剂可增强其对化疗和ICI的治疗反应。例如,有一项研究证明 CTLA-4 已被用于免疫治疗,然而其抗肿瘤疗效被几种 Bactaroidetes 菌属阻断。
因此,他们使用了多形拟杆菌和/或脆弱拟杆菌与CTLA-4联合治疗,通过免疫刺激作用观察CTLA-4 的抗体靶向作用。同样,Sivan等证明双歧杆菌可通过其对小鼠 PD-L1的免疫调节作用增强肿瘤控制。当双歧杆菌与ICI联用时,几乎可以完全抑制肿瘤生长[21]。此外,通过选择合适和潜在的微生物组,TNBC进展可以通过改变饮食习惯、修改粪便微生物环境和使用益生菌来进行逆转,联合使用其他潜在的微生物组也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疗效和总生存期缓解率。
结论和未来展望
TNBC约占BC患者总人群的20%,是最具挑战性的乳腺癌亚型。过去十年中,多种常规的治疗策略并不能为这些患者提供实质性获益,大多数人群容易复发。多种因素导致了TNBC的侵袭性。一些基因突变、细胞驱动因子、代谢改变、表观遗传失调、信号通路过表达、细胞表面受体和免疫调节的突变使得TNBC对放疗和化疗的反应性降低,因此,TNBC容易发生复发和转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案。
全球科学界在TNBC治疗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结果来看,其治疗似乎颇具前景。相关结果表明,我们亟需解决异质性肿瘤微环境、受试者间和受试者内变异性、肿瘤间和肿瘤内异质性、肿瘤干细胞的作用和相关修饰以及表观遗传学变化等问题。随着我们对肿瘤认知不断加深,除手术、放疗和化疗外,未来还需要探索其他治疗途径,如基因编辑技术、光动力疗法、治疗诊断学、生物制剂和生物电子药物,来作为上述一种或联合治疗方案。组合方案的开发将有助于实现广泛的TNBC治疗,包括用于预防复发、转移和化疗耐药。当然,我们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开发出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案,使其毒性组分更低,如采用复合受体来递送生物活性成分,靶向纳米药物或可提供所有这些获益。
[1] Feng Y, Spezia M, Huang S, et al. Breast cance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risk factors, cancer stem cells, signaling pathways, genomics, and molecular pathogenesis. Genes Dis 2018;5:77–106.
[2] Kumar H, Gupta NV, Jain R, et al. A review of biological targets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es in the management of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J Adv Res. 2023 Feb 14:S2090-1232(23)00056-5.
[3] Gooding AJ, Schiemann WP.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programs and cancer stem cell phenotypes: mediators of breast cancer therapy resistance. Mol Cancer Res 2020;18:1257–70.
[4] Schmit K, Michiels C. TMEM proteins in cancer: a review. Front Pharmacol 2018;9. doi: https://doi.org/10.3389/fphar.2018.01345.
[5] Xiao H, Zheng Y, Ma L, Tian L, Sun Q. Clinically-relevant ABC transporter for anti-cancer drug resistance. Front Pharmacol 2021;12. doi: https://doi.org/ 10.3389/fphar.2021.648407.
[6] Hamed AR, Abdel-Azim NS, Shams KA, Hammouda FM. Targeting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cancer by natural chemosensitizers. Bull Natl Res Cent 2019;43. doi: https://doi.org/10.1186/s42269-019-0043-8.
[7] Wu S, Fu L.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nhanced the efficacy of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eutic agent in multidrug resistant cancer cells. Mol Cancer 2018;17. doi: https://doi.org/10.1186/s12943-018-0775-3.
[8] Steward LT, Gao F, Taylor MA, Margenthaler JA. Impact of radiation therapy on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Oncol Lett 2014;7:548–52. doi: https://doi.org/10.3892/ol.2013.1700.
[9] Tang L, Wei F, Wu Y, He Y, Shi L, Xiong F, et al. Role of metabolism in cancer cell radioresistance and radiosensitization methods. J Exp Clin Cancer Res 2018;37. doi: https://doi.org/10.1186/s13046-018-0758-7.
[10] Menaa C, Li JJ. The role of radiotherapy-resistant stem cells in breast cancer recurrence. Breast Cancer Manag 2013;2:89–92.
[11] Bai X, Ni J, Beretov J, et al. Activation of the eIF2a/ATF4 axis drives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radioresistance by promoting glutathione biosynthesis. Redox Biol 2021;43.
[12] Bai X, Ni J, Beretov J, et al. THOC2 and THOC5 regulate stemness and radioresistance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Adv Sci 2021;8. doi: https://doi.org/10.1002/advs.202102658.
[13] Yang L, Shi P, Zhao G, et al. Targeting cancer stem cell
pathways for cancer therapy.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0;5. doi: https://doi.org/10.1038/s41392-020-0110-5.
[14] Sun HR, Wang S, Yan SC, et al.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argeting cancer stem cells and their microenvironment. Front Oncol 2019;9.
[15] Jain V, Kumar H, Anod HV, et al. A review of nanotechnology-based approaches for breast cancer an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J Control Release 2020;326:628–47.
[16] Pascual T, Gonzalez-Farre B, Teixidó C, et al. Significant clinical activity of olaparib in a somatic BRCA1-mutate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with brain metastasis. JCO Precis Oncol 2019;3:1–6.
[17] Ha K, Fiskus W, Choi DS, et al.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treatment induces “BRCAness” and synergistic lethality with PARP inhibitor and cisplatin against huma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Oncotarget 2014;5:5637–50.
[18] Yu J, Zayas J, Qin B, Wang L. Targeting DNA methylation for treating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Pharmacogenomics 2019;20:1151–7.
[19] Kang HJ, Yi YW, Hou SJ, Kim HJ, Kong Y, Bae I, et al. Disruption of STAT3-DNMT1 interaction by SH-I-14 induces reexpression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s and inhibits growth of triple-negative breast tumor. Oncotarget 2017;8:83457–68.
[20] Guarneri V, Dieci MV, Conte P. Relapse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hallenge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Drugs 2013;73:1257–65.
[21] Sivan A, Corrales L, Hubert N, et al. Commensal Bifidobacterium promotes antitumor immunity and facilitates anti–PD-L1 efficacy. Science (80-) 2015;350:1084–9.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Paine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