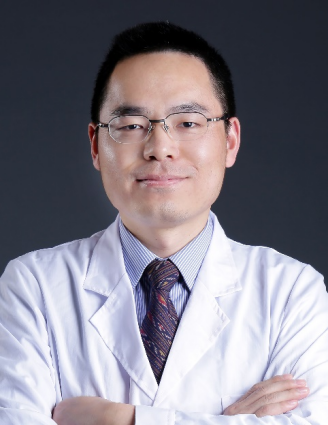2022年CSCO结直肠癌专委会年会虽已过去数月,但余音绕梁怎可三日而止。在该次盛大的学术会议上,五湖四海的结直肠癌领域国内顶尖专家汇聚一堂,共话前沿进展。
其中,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任黎教授带来的【直肠癌肝转移】病例报告,引得多位专家一齐讨论,火花不断。【肿瘤资讯】将内容整理如下。
专家简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结直肠外科 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肿瘤诊疗规范推广应用专委会 委员兼外科组组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结直肠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专业委员会外科学组、肝转移学组、亚微学组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 结直肠外科医师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炎性肠病医师分会 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遗传学组委员
精彩视频
点击视频查看病例讨论精彩瞬间
患者病史
患者女,33岁,于2020年10月因“剖宫产术中发现子宫后实性包块2周”外院就诊后两周住院。该患者体型瘦小,查体未见明显阳性体征;直肠指检示距肛缘7cm肿块,占肠腔2/3圈。既往有甲减史、剖宫产史、青霉素过敏史。

肠镜病理检查为腺癌,基因检测示微卫星稳定(MSS)、HER阴性、全野生型。

基线检查如下。

PET-CT检查显示盆腔中有一个糖代谢非常高的区域,肿块大小足足有十公分。

主要的MRI层面呈现如下,较为明显。

首次MDT诊疗
首次多学科(MDT)诊断如下。

由于该病人考虑为晚期直肠癌,临床分期为cT4N+M0;考虑到手术切除无法完全根治,故先行放化疗。
首次治疗及随访情况如下。

2021年4月份进行了第一次复查,结果显示,较去年10月份有所好转;之前肿瘤标志物对于该疾病的反应并不敏感,但此次复查CEA水平恢复到一个较低水平。

此次复查盆腔MRI示,该肿块虽仍较大,但较之前已有缩小,说明放化疗有一定疗效。去年10月份和今年4月份的检查结果对比如下。

第二次MDT诊疗
第二次进行MDT讨论,疗效评估为原发灶缩小(PR),但由于该病灶范围广泛、侵袭周围病灶较广,考虑到手术难以达到R0切除的标准,故基于其全野生型的基因检测结果,为患者在放化疗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添加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OX治疗(四周期)。

 2021年6月份进行复查,示原发肿块之前稍有进展,关键之处在于:发现了肝左内叶转移灶,同时肿瘤指标(CEA)也开始攀升。
2021年6月份进行复查,示原发肿块之前稍有进展,关键之处在于:发现了肝左内叶转移灶,同时肿瘤指标(CEA)也开始攀升。

从MRI上可见肝左叶一个明显的转移灶。对比4月份和6月份的MRI关键层面MRI图更为明显。
 从腹盆腔CT可明显看出,肝左内叶包膜下的低密度灶,直径约15mm。
从腹盆腔CT可明显看出,肝左内叶包膜下的低密度灶,直径约15mm。

第三次MDT诊疗
第三次MDT讨论为原发灶稍增大(SD)、肝新发转移灶,总体表现为疾病进展(PD)。此时患者已出现梗阻问题,故建议先接触梗阻再将全身治疗方案调整为贝伐珠单抗联合FOLFIRI治疗。

具体治疗过程如下。

2021年8月份进行第4次复查,从CEA水平不断上升可见,患者情况不甚良好,同时原发灶有所进展、肝脏出现多发转移灶。
 从盆腔MRI可见,原发肿块继续增大;而从上腹部MRI可见,肝脏不仅在左叶有转移灶,右叶亦可见两个转移灶。
从盆腔MRI可见,原发肿块继续增大;而从上腹部MRI可见,肝脏不仅在左叶有转移灶,右叶亦可见两个转移灶。
对比两次MRI:原发灶持续增大,但增大速度不及肝转移灶快。因此疾病进展较为明显。

第四次MDT诊疗
第四次MDT讨论为原发灶稍增大(SD),肝转移灶明显进展,总体为PD。建议对该患者行肝内介入治疗,并行穿刺以进行下一代基因测序(NGS)。

治疗及检测结果如下:示肝转移灶基因分型大致与原发灶一致,但其提示肿瘤突变负荷(TMB)高,可尝试使用免疫治疗。
具体治疗如下。

 第五次复查示,CEA水平仍久升不跌,原发灶较前进展,但肝多发转移灶较前有所缩小,证实有所疗效。
第五次复查示,CEA水平仍久升不跌,原发灶较前进展,但肝多发转移灶较前有所缩小,证实有所疗效。 盆腔MRI示肿块较前增大,上腹部MRI示肿块较前有所缩小。
盆腔MRI示肿块较前增大,上腹部MRI示肿块较前有所缩小。

两次MRI结果对比如下。
肝脏MRI如下。

第五次MDT诊疗
第五次MDT讨论结果如下。
 尽管当时决定行原方案的治疗,但后续发现病人甲减复发,因此仅能暂停特瑞普利单抗的治疗。
尽管当时决定行原方案的治疗,但后续发现病人甲减复发,因此仅能暂停特瑞普利单抗的治疗。

三周期后,患者出现尿频、排尿困难,故请泌尿外科协助会诊,有所改善。

第六次复查结果显示,CEA水平增长非常快,并且原发灶局部进展明显;但肝脏转移灶则明显缩小。
 盆腔MRI如下。
盆腔MRI如下。

第五次MDT诊疗
第六次MDT讨论为建议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IRI原方案治疗(四周期)。

具体如下。
 很遗憾的是,由于疫情反复,该患者未能及时复查,导致后续随访数据丢失。
很遗憾的是,由于疫情反复,该患者未能及时复查,导致后续随访数据丢失。
病历小结

嘉宾点评

图:专家讨论群像(来源CSCO官网)
钱晓萍教授:该病例诊疗过程较为规范,但十分具有挑战性。但新辅助放疗标准年限、原发灶是否该行NGS检测、新辅助放化疗后是否尝试肠镜探查、肝转移灶行介入治疗的同时,原发灶是否应行减瘤治疗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讨论。
韩方海教授:从外科医生的角度而言,如何把外科手术与新辅助放化疗或放化疗联合免疫、靶向治疗结合在一个最佳点上,何时该手术干预、何时该使用药物是一个难题。
王巍教授:对于此类在临床上生存希望不大的患者,临床上会积极采取强效三联/四联药物尽力为患者争取一线生机;在患者身体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添加例如替尼类或TAS-102药物。但该类药物的三线、四线治疗方案的指导依据有哪些?是否有分子特征可进行适宜人群的参考?这些问题需要未来实践去多多探索。
王启峰教授:原发肿瘤在血行转移之前,若使用强效的三联化疗方案,结局会否与现在有所不同?
唐勇教授:值得注意的是,原发灶的进展和转移灶的好转不同步,在此需要注意是否有假进展的可能性;其次,虽然病人出现了甲减,但是否可以在加用优思乐的基础上进行免疫治疗?这些都值得思考。
刘莺教授:诸位专家讨论的关键点在于,我们认为最为规范的治疗却对于患者来说却并非最为获益。
看完了本篇病例讨论,您作何感想?请在下方留言告诉小编您的见解!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B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