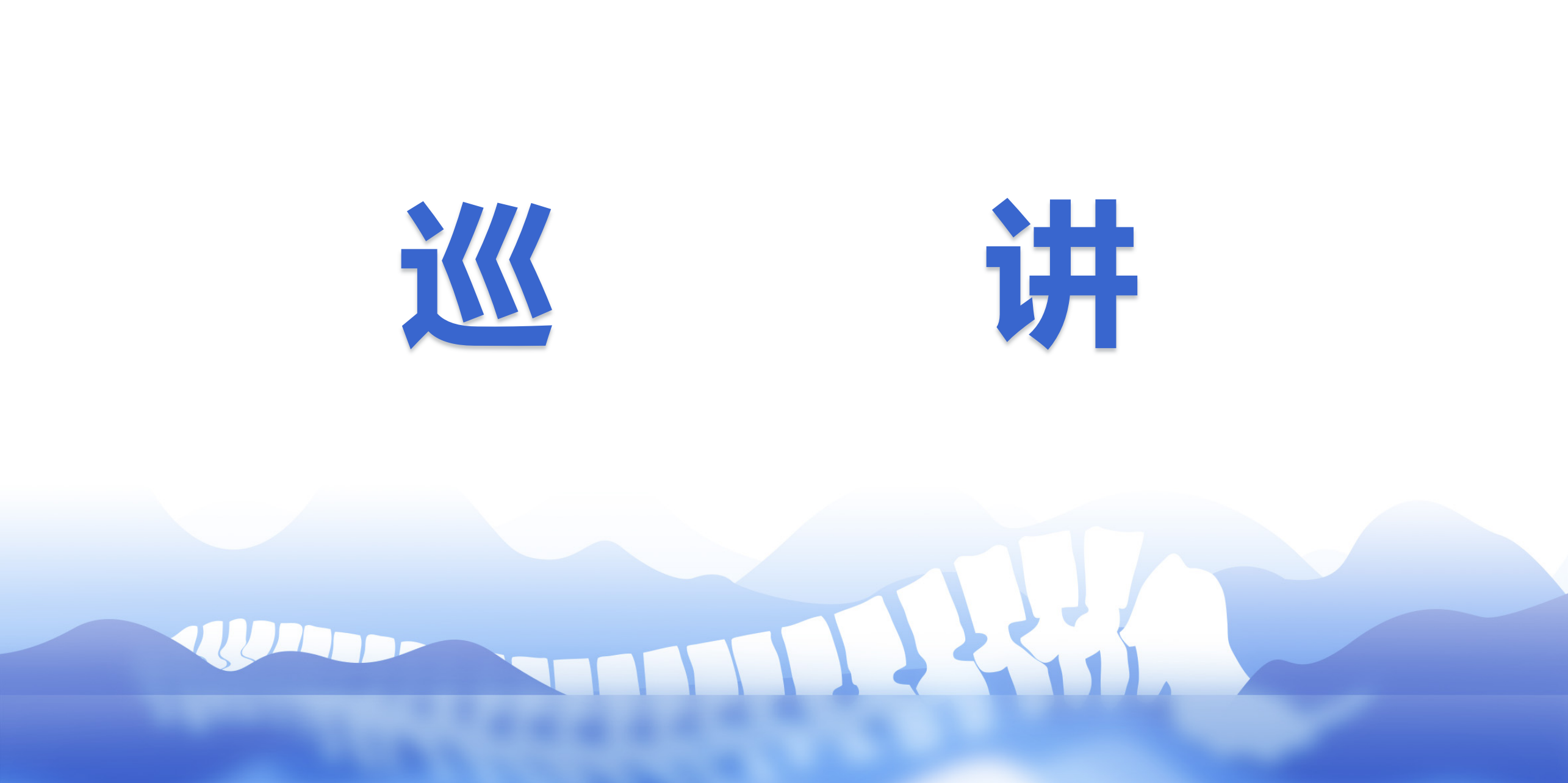全球及中国消化道肿瘤疾病负担仍然很重,呈现发病率、死亡率双高的特征。但近年免疫治疗的发展为消化道肿瘤带来新的契机,并改变了消化道肿瘤治疗的格局。但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免疫治疗近五年发展迅猛,我们仍面临众多临床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刘天舒教授将带我们回顾消化道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和适应症获批情况,并就临床实践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今年相关医药政策的更新,畅谈创新药物研发的方向和挑战。
特邀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肿瘤教研室主任,肿瘤早期研究病房主任,伦理委员会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防治中心秘书长
上海市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专科第七届主任委员
上海市肿瘤化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CSCO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委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CSCO临床研究专委会/胃癌专委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大数据与真实世界研究专委会常委
上海市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分会常委
中国老年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常委
获“第四届国之名医·优秀风范”、第三届“仁心医者·上海市杰出专科医师奖”、第三届“上海最美女医师”等荣誉称号
中国消化道肿瘤疾病负担重,发病率和死亡率双高
全球范围内消化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情况如下:结直肠癌分别为第4位和第5位,胃癌均为第6位,食管癌分别为第11位和第7位;同时,中国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肿瘤负担同样很重,呈现发病率、死亡率“双高”的特征。中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居第3位和第5位,胃癌为第4位和第3位;食管癌则为第6位和第4位[1]。

消化道肿瘤的诊治具有一定复杂性。不同的起源组织导致了一系列不同的疾病,如结直肠癌、胃癌都有其特定的临床特征。而基因组和转录组分析通过识别所谓的分子亚型进一步定义了存在于这些癌症中的异质性[2]。因而,每种类型的消化道肿瘤在分子亚型和起源上,都是独特的。同时消化道肿瘤在中西方人群中所表现出极强的异质性,也使得我们无法照搬西方研究数据与治疗方案。我国在以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为代表的消化道肿瘤上面临着巨大的治疗瓶颈,总体生存率较乳腺癌差距较大,生存获益不理想[3]。
消化肿瘤免疫治疗发展方向与挑战
然而,免疫治疗,尤其是如PD-1、PD-L1这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发现,为消化道肿瘤的治疗带来了曙光。自2018年以来,免疫治疗相关数据变得尤为丰富,基于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逐步改变了消化道肿瘤的治疗格局,CSCO食管癌、胃癌及结直肠癌指南中对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推荐等级逐步前移,给了临床医生更多实践选择,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消化道肿瘤的治疗困境。
实际上,临床研究、适应症和临床实践是任何治疗领域中密不可分的三个重要因素,但并未完全匹配。尽管免疫治疗在近5年来发展迅猛,但仍面临众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免疫治疗方案的优化
从KEYNOTE-590、KEYNOTE-062、KEYNOTE-181研究中,我们已看到免疫治疗在部分患者身上的疗效,但仍未达到理想状态。免疫治疗组与化疗组的生存曲线最终还是达归零状态,而非保持恒定、持续、平稳的状态。这就要求临床设计时应进一步优化治疗模式,以在更有针对性的人群达到更高的疗效。
免疫治疗优势人群的选择
在KEYNOTE系列研究,甚至包括CheckMate-649等研究, PD-L1 CPS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物标志物,CPS评分高的患者可从免疫治疗获得进一步的生存改善。同时基于KEYNOTE-177和KEYNOTE-158等研究,MSI-H/dMMR人群也适于接受免疫治疗。此外,HER2+、TMB、等生物标志物在消化道肿瘤的免疫治疗均有探索,我们也期待不断扩展和提升生物标志物的疗效预测作用。
免疫治疗介入的最佳时机和应用模式
目前而言,在消化道肿瘤中,MSI-H人群基于免疫单药的治疗可获得较好的疗效,但多数情况下,消化道肿瘤仍是采取免疫联合模式。免疫介入的时机也存在争议,从原理上而言,放化疗后释放的肿瘤相关抗原可能会激活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但是否真的在化/放疗后再应用免疫能够提高疗效仍有待相关研究的验证。
irAE的早期识别
irAE是免疫治疗过程中亟需关注的。多种细胞因子、血液细胞成分和肿瘤免疫组学等和irAE发生的相关性均有探索,但目前仍尚未明确。
超进展或原发耐药人群的早期识别
超进展是免疫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研究者试图基于临床指标、肿瘤微环境和细胞生物标志物(如MDM2扩增、EGFR突变、BRCA2突变等)找出能够预测并避免超进展发生的可靠指标。这也是促进精准治疗亟需解决的。在原发性耐药的探索上,目前认为潜在生物标志物有PD-L1阴性表达、新抗原或突变负荷低、获得性新抗原减少、肿瘤实质TIL水平低、MDSC循环频率增加、IDO水平下降、IFN‐γ通路中的有害突变增加[4],此外,研究已证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热”肿瘤中更具活性,其中,“热”肿瘤的特征是显著的间质淋巴浸润和高密度的TIL,且伴有炎症细胞因子丰富的微环境和T细胞炎症的基因表达谱[5]。
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的空白亟需填补
临床研究、适应症获批或指南推荐及临床实践三者间仍有空白,如何找到并填补这个空白是未来免疫治疗发展将面临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临床医生在实践中可能面临下述问题:
临床研究vs 临床实践:基于研究数据写进指南推荐的方案在真实临床场景中应用时仍会面临各种问题。对于临床研究中没有覆盖到的、多样化的临床实践场景,临床医生应如何用好相关数据?对于超过临床研究的场景(如临床试验以外的或非高度筛选的人群等),相关方案是否继续适用?这是肿瘤规范化治疗中又一挑战。
亚组分析结果对临床实践的影响: 在大型临床研究中,亚组分析可帮助更为精准地找出有效/无效人群,但亚组分析的样本量较小且统计学意义较弱,理论上其结果不足以指导临床决策。但同时我们也看到KEYNOTE-177纳入所有MSI-H/dMMR人群,而因中国人群数据缺失,中国国家药监管理局(NMPA)仅批准了其用于MSI-H/dMMR且KRAS/NRAS/BRAF全野生型的中国人群的适应症。因此,我们应谨慎看待亚组分析结果的价值。
临床研究设计和临床实践间的空白:临床研究设计通常有严格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例如RCT研究中通常只纳入身体状况良好且无明显合并症的患者[6],而真实世界中存在很多并不符合高标准筛选条件的患者。如约20%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因体能状态不佳而未纳入临床研究[7],而体能状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填补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的空白也属当务之急。
客观看待Ⅱ期探索性研究:一般而言,被写入指南推荐的治疗方案多基于Ⅲ期研究数据,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探索性Ⅱ期研究数据被写入指南。如PALACE-1、NICE等研究对食管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探索,及REGONIVO 研究对MSS型结直肠癌免疫联合的探索,均获得可观的疗效。但Ⅱ期研究样本量往往很小,旨在探索研究方案是否可行,若想要进一步成为推荐级别较高的可行方案,仍需通过开展Ⅲ期研究以进一步确认。对于Ⅱ期研究数据,临床上是否可以尝试,若尝试如何把握尺度则是临床医生关心的。
临床或疾病需求对不同疾病阶段中临床研究设计终点选择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针对不同的临床模式,研究终点的选择不同。对于晚期前线研究,通常选用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作为研究终点;晚期后线研究则选用客观缓解率(ORR)或持续缓解时间(DOR);辅助治疗则选择无病生存(DFS)和新辅助治疗以病理完全缓解(pCR)或主要病理缓解(MPR)。另外,观察到的研究终点所需要的时间,不同研究终点所分配的α及其效能等也会成为选择终点时的考量因素。
小结:政策利好,发展前景广阔
目前,中国和全球消化道肿瘤免疫治疗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但研究者应该对临床情况有一个充分的认知,以设计出适用于临床场景所需要的研究。调研发现,我国在研新药数量与相应疾病负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在中国的first-in-class产品管线中,免疫肿瘤领域有大量的候选药物,同时细胞疗法也是研究的热点[9]。
随着中国药监部门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并当选管委会成员,中国药品注册管理制度正加速与国际接轨。目前,全球及我国医药研发呈现出良好的形势,国家连续出台的系列政策更是促进了创新药的研发。2021年一系列医药政策的发布也将对临床研究的开展产生深远影响——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抗肿瘤药物研发,以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为药物研发的初心。此外,我们的新药研发也正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且药物临床适应性设计指导原则的发布也有望提升临床试验的效率,与此同时,药物审批提速,也将为创新药物在中国上市插上翅膀,更快惠及患者。
[1] https://gco.iarc.fr/today/fact-sheets-cancers.
[2] Bijlsma MF, Sadanandam A, Tan P, et al. Molecular subtypes in cancers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7 Jun;14(6):333-342.
[3] Zeng H, et al. Lancet Glob Health. 2018 May;6(5):e555-e567.
[4] Chae YK, Oh MS, Giles FJ. Oncologist. 2018 Apr;23(4):410-421.
[5] Puccini A, et al. J Immunother Cancer. 2020 May;8(1):e000404.
[6] Batra A, Cheung WY. Role of real-world evidence in informing cancer care: lesson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Curr Oncol. 2019 Nov;26(Suppl 1):S53-S56.
[7] Travers A, Jalali A, Begbie S, et al. Real-World Treatment and Outcomes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a Poor or Very Poor Performance Status. Clin Colorectal Cancer. 2021 Mar;20(1):e21-e34.
[8] Ronellenfitsch U, Jensen K, Seide S, et al. Disease-free survival as a surrogate for overall survival in neoadjuvant trials of gastro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Pooled analysis of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from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Eur J Cancer. 2019 Dec;123:101-111.
[9] Li G, Qin Y, Xie C, Wu YL, Chen X. Trends in oncology drug innovation in China. Nat Rev Drug Discov. 2021 Jan;20(1):15-16.
MI-PD1-2106-CN ;
过期日期:2022年10月25日
本资讯由默沙东医学团队提供,旨在用于医学专业人士间的学术交流,请勿随意转发或转载。文中相关内容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治疗建议。医学专业人士对文中提到的任何药品进行处方时,请严格遵循该药品在中国批准使用的说明书。默沙东不承担相应的有关责任。
排版编辑:Phoebe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