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外科 博士、主治医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青年分会 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规范化诊治江西培训基地 秘书
江西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 青年委员
江西省整合医学学会肥胖和代谢病分会 委员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中青年编委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特约编辑
《Translation Cancer Research》 Section Editor
江西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
主持江西省其他省部级课题2项,参与其他各类课题研究10余项
以单独一作或通讯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SCI6篇(最高IF 8.0)
2020年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女性乳腺癌已超越肺癌成为全球头号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及
死亡率约占所有恶性肿瘤的11.7%与6.9%,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严重威胁女性健康[1]。其 中,三阴性乳腺癌(TNBC)约占乳腺癌总数的10%-20%[2],因不表达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对临床内分泌治疗及抗HER-2靶向治疗均无效,化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尽管TNBC对化疗相对敏感,但与其他亚型乳腺癌相比,它仍然具有不良临床分期、高复发转移、短生存期与易发生化疗耐药等临床特点[2],寻找新的治疗方式迫在眉睫。
目前,较多实体瘤的临床研究相继证实免疫治疗可有效提高患者疗效及生存期,这种治疗方式也有望为TNBC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事实上,与其他亚型的乳腺癌相比,TNBC免疫原性更强,伴随的肿瘤突变负荷更大、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更多、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1/PD-L1)表达水平更高[3-4],提示TNBC更有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正因如此,TNBC免疫治疗的大幕正徐徐拉开。近年来已开展了多项TNBC免疫治疗相关的临床研究,其中PD-1/PD-L1抑制剂在TNBC免疫治疗的探索已初露曙光,逐渐成为晚期TNBC(mTNBC)解救治疗和早期TNBC(eTNBC)新辅助及辅助治疗的重要临床方案。本文就当前免疫治疗在mTNBC和eTNBC的相关研究进展及TNBC免疫治疗的未来方向等方面作一总结并陈述笔者的临床观点及看法,如有错误之处,望评审专家海涵并不吝指教。
一、mTNBC与免疫治疗
广义而言,临床免疫治疗主要包含以下几类:①、主动免疫的肿瘤疫苗治疗:如树突状疫苗、肽疫苗、HIF-1a疫苗、癌-睾丸抗原疫苗等,这些肿瘤疫苗目前有一定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多处于体外研究阶段,有赖于更多的体内研究证实;②、过继性免疫治疗:如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T)、细胞因子诱导杀伤(CIK)、自然杀伤(NK)等细胞治疗,这些治疗手段在淋巴瘤及血液系统肿瘤中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实体瘤中还有待更多的临床验证;③、间皮素治疗、溶瘤病毒治疗:同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尚缺乏体内研究的证据;④、免疫检查点阻断剂治疗:如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PD-1/PD-L1、唾液酸结合性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15(Siglec15)等:其中CTLA-4抑制剂与Siglec15抗体在mTNBC中的II期临床研究仍在进行中,数据尚不成熟;但PD-1/PD-L1抑制剂免疫治疗与mTNBC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涉及,以下我们将做详细探讨。
1、PD-1/PD-L1抑制剂单药解救治疗
目前已报道的PD-1/PD-L1抑制剂单药解救治疗mTNBC相关临床研究主要包括PCD4989g研究与KEYNOTE-012/086/119等系列研究。其中,PCD4989g是一项小样本量Ⅰ期单臂临床研究,旨在评估阿替利珠单抗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和血液肿瘤中的安全性和抗肿瘤活性。结果表明,对于晚期或转移性TNBC患者,阿替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耐受性良好、临床获益持久,尤其是对于肿瘤免疫细胞浸润较高的患者[5]。此外,KEYNOTE-012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非随机Ib期研究,旨在评估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晚期PD-L1阳性TNBC、晚期胃癌、晚期膀胱上皮癌和晚期头颈部癌症患者的安全性及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在27例疗效可评估的TNBC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RR)为18.5%,包括1例(3.7%)完全缓解和4例(14.8%)部分缓解,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中位总生存期(OS)分别为1.9个月和11.2个月[6]。而II期KEYNOTE-086研究进一步评估了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mTNB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A队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既往经治过的mTNBC患者)的ORR仅为5.3%,B队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PD-L1阳性mTNBC患者)的ORR达21.4%,两队列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2.1个月和18.0个月[7]。遗憾的是,在随后的III期临床试验KEYNOTE-119研究中,与单药化疗相比,在先前接受过治疗的mTNBC患者中(允许既往1-2线系统治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并未显著改善ORR(总人群约10%)、PFS以及OS,但在这些疗效终点中,随着肿瘤PD-L1表达的增加,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效果有升高的趋势[8]。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这些已经达到2-3线的mTNBC患者,虽然PD-1/PD-L1抑制剂不优于化疗,但同样不劣于化疗,并且与化疗组相比有着更低的不良反应,临床耐受性更好,在mTNBC解救治疗中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总体而言,我们不难看出:mTNBC患者应用PD-1/PD-L1抑制剂单药解救治疗ORR并不高,大约维持在10%-20%;然而,一旦患者对免疫治疗起效,其持续缓解时间显著延长。因此,与PD-1/PD-L1抑制剂搭配其他方式的治疗(序贯或同步)则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II期TONIC临床研究则在PD-1/PD-L1抑制剂序贯治疗中做出了相关探讨:这是一项开放性、随机非盲、对接受≤3线姑息性化疗后进展的mTNBC患者行短疗程放疗或低剂量化疗诱导后给予纳武利尤单抗的疗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接受顺铂及多柔比星诱导化疗的患者,纳武利尤单抗单药解救治疗的ORR有所提高,分别为23%及35%,对于免疫治疗有效的患者1年OS率高达85%,显著高于无效患者(18%)[9]。而在2019年后续的分子研究探索中可以看到,顺铂及多柔比星显著诱导患者体内肿瘤免疫微环境成分改变,纳武利尤单抗解救治疗有效的TNBC患者中TILs和CD8+T细胞的比率更高[10]。因此,把相对“冷”的乳腺肿瘤诱导为相对“热”的肿瘤亚型,从而进一步提高免疫治疗的ORR,将有望使更多的TNBC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相信更多的免疫治疗诱导方式会在未来的临床研究中被探讨。
2、PD-1/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解救治疗
PD-1/PD-L1抑制剂免疫单药解救治疗在mTNBC中的探索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而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其他更多治疗手段的联合是值得关注的治疗思路,化疗则成为了临床研究中的主流搭档。首先,GP28328是一项探索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在mTNBC中的安全性和疗效的多中心Ib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人群ORR为39%,接受一线治疗的患者和PD-L1阳性的患者可获得更高的ORR,总体人群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5.5个月和14.7个月,该研究显示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以及良好的抗肿瘤活性[11]。然而,真正开启了mTNBC免疫治疗新时代的是IMpassion130研究:它是首个免疫治疗在mTNBC的Ⅲ期临床研究中取得阳性结果的临床试验,该研究旨在评估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对比安慰剂联合白蛋白紫杉醇一线治疗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NBC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结果显示,在ITT人群中,阿替利珠单抗组对比安慰剂组PFS显著延长,两组中位PFS分别为7.2个月和5.5个月(P=0.0025);尤其在PD-L1阳性患者中,两组中位PFS分别为7.5个月和5.0个月(P<0.0001)[12],提示PD-L1阳性患者从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紫杉醇方案中的获益更大。2020年ESMO年会上进一步更新了OS数据:在PD-L1阳性患者中,阿替利珠单抗组的中位OS为25.4个月,较安慰剂组(中位OS为17.9个月)达到了7.5个月的显著改善,且安全性良好[13]。此外,另一项双盲、随机对照、多中心的III期临床试验KEYNOTE-355研究也得到了类似数据[14]:研究旨在评估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对比安慰剂联合化疗用于初治的局部复发不可手术或转移性TNBC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对于PD-L1阳性[综合阳性评分(CPS)≥10]的人群,帕博利珠单抗组PFS显著延长(9.7 vs 5.6个月,P=0.0012);而对于CPS≥1的人群,帕博利珠单抗组的PFS虽有延长(7.6 vs 5.6个月),但未达统计学差异。根据CPS的界值不同,亚组分析还发现,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在CPS≥20的人群中获益最为显著,其他依次为CPS≥10的人群和CPS≥1的人群,总体来说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组耐受性良好。正是因为上述研究进展,在2021版的CSCO指南更新中,将mTNBC解救治疗的方案选择加入了白蛋白紫杉醇联合PD-1/PD-L1抑制剂(II级推荐,2A类证据)与化疗联合PD-1抑制剂(III级推荐,2B类证据),可见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诊疗模式正逐步改变mTNBC的临床实践。
有趣的是,正当大家认为PD-1/PD-L1抑制剂免疫治疗即将在mTNBC解救治疗中大放异彩的时候,IMpassion131研究无疑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它是一项评估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一线治疗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NBC的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该研究设计基本与IMpassion130研究类似,主要区别在于化疗药物的不同(一个是白蛋白紫杉醇,另一个是普通溶剂型紫杉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IMpassion131研究未能获得预期结果:与安慰剂组相比,阿替利珠单抗组未能显著改善PFS;此外,无论是在PD-L1阳性人群还是在总体人群中,中期OS结果却都更支持单药紫杉醇[15]。这两项“姊妹”研究提示我们,TNBC群体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免疫治疗联合化疗仍面临很多挑战,如何选择免疫治疗的最佳时机、最佳联合拍档和优势获益人群,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3、PD-1/PD-L1抑制剂联合其他治疗
除了与化疗同步联合之外,其他的免疫联合治疗方式也值得探索。II期TOPACIO(KEYNOTE-162)试验旨在评估PARP抑制剂尼拉帕利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晚期或转移性TNBC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在47例疗效可评估的患者中,10例患者达到客观缓解(21%),23例患者获得疾病控制(49%);且无论BRCA突变状态如何,尼拉帕利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晚期或转移性TNBC患者中均显示出有潜力的抗肿瘤活性,并具有较好的安全性[16]。另一项II期COLET研究探索了MEK抑制剂考比替尼(cobimetinib)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和紫杉类化疗的三药方案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NB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该三联方案仅表现出适度的临床缓解,且在PD-L1阳性人群中更明显。考比替尼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和紫杉醇组的ORR为34.4%,考比替尼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和白蛋白紫杉醇组的ORR为29.0%;两组中位PFS分别为3.8个月和7.0个月[17],联合白蛋白紫杉醇组虽然ORR稍低,但PFS时间似乎更长,这与IMpassion130/131研究所得到数据类似。
抗血管生成药物同样可作为免疫治疗的药物拍档。在一项Ⅱ期临床试验中纳入了40例晚期接受化疗<3线的mTNBC患者均接受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其中30例阿帕替尼为连续剂量(每日服用250mg),10例阿帕替尼为间断剂量(每日服用250mg,口服一周停一周)。结果显示,总体人群的ORR为57.5%,其中连续剂量组ORR高达63.3%,而间断剂量组ORR仅40%(PR率甚至为0)[18]。欣喜的是,笔者近期曾在临床实践中对一例晚期5线治疗后已对多种化疗、阿帕替尼及奥拉帕尼耐药的TNBC患者尝试使用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治疗,我们意外发现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解救治疗方案可持续缓解患者肺部及脑部病灶(至今PFS已达7个月,超过前线任何一次的解救治疗缓解时间),且患者生活质量及药物耐受性极好,目前该患者仍在持续随访中。事实上,PD-1/PD-L1抑制剂联合安罗替尼的治疗效果在晚期肺癌、卵巢癌等“热”肿瘤中早已得到相关证实,而深究药物作用机制不难发现,安罗替尼不仅有多靶点(VEGFR、PDGFR、FGFR等)抗血管生成作用,还可重塑肿瘤微环境进而解除免疫抑制状态及增加T细胞活性与浸润,有潜在协同免疫治疗的效应。此外,笔者从多个mTNBC患者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安罗替尼+的方案(可联合化疗、免疫治疗、PARP抑制剂等)解救有效率较高,且与阿帕替尼无明显交叉耐药,药物副反应显著低于阿帕替尼,药物中断率低,患者依从性好,临床潜在适用性佳(本中心数据尚在统计中,待后续报道)。然而,查阅文献后我们发现安罗替尼应用于mTNBC中的大样本数据少之又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设计PD-1/PD-L1抑制剂联合安罗替尼在mTNBC解救治疗或维持治疗中的疗效及安全性的相关临床研究,两者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或有望为部分难治性mTNBC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同时,乳腺癌相关疫苗联合PD-1/PD-L1抑制剂的多项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PVX-410疫苗(NCT03362060),叶酸受体α疫苗(NCT03012100)和新肿瘤抗原疫苗(NCT03606967)。此外,免疫抑制剂联合溶瘤病毒(NCT03004183)和过继细胞疗法(TILs转移,NCT04111510;CAR-T,NCT02792114)等研究也正在火热开展中。
二、eTNBC与PD-1/PD-L1抑制剂新辅助治疗
既往研究显示,病理学完全缓解(pCR)与TNBC新辅助治疗结局相关,在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的TNBC患者临床获益明显[19]。TNBC患者中以紫杉和蒽环为基础的新辅助治疗方案的pCR率约为40%[20],添加铂类药物可使pCR率提高至50%-60%[21]。临床荟萃分析进一步显示,TNBC患者新辅助化疗后pCR率的提高与长期EFS和OS的获益显著相关[22]。
PD-1/PD-L1抑制剂在eTNBC中的新辅助治疗研究亦进行的如火如荼。Ib期临床试验KEYNOTE-173研究评估了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在TNBC新辅助治疗中的安全性和初步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联合卡铂,帕博利珠单抗新辅助治疗对局部晚期TNBC患者都具有令人鼓舞的抗肿瘤活性,且不会增加严重毒性作用[23]。随后,II期临床试验I-SPY2研究证实,与单纯化疗相比,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可明显改善eTNBC患者的pCR率[24]。更进一步,Ⅲ期临床研究KEYNOTE-522的实验结果振奋人心:这是一项探索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新辅助(方案为紫杉醇联合卡铂序贯多柔比星/表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序贯帕博利珠单抗辅助治疗的方案对eTNBC患者治疗的疗效。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总体人群还是PD-L1阳性/阴性人群,含铂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新辅助方案较化疗能够进一步提高pCR率[25]。更重要的是,在帕博利珠单抗新辅助治疗后的辅助治疗阶段,继续使用帕博利珠单抗较安慰剂能够提高EFS。深入探讨KEYNOTE-522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该研究的新辅助化疗方案在标准的紫衫联合蒽环方案上加入了铂类药物,参考GeparSixto与CALGB 40603研究我们知道以上化疗方案的pCR率已经非常高(超过50%),而该方案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免疫治疗还可进一步提高患者pCR率(超过60%),部分PD-L1阳性人群中pCR率甚至接近70%,且并未带来明显不良反应,可见PD-1/PD-L1抑制剂免疫治疗在eTNBC新辅助治疗中同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未来可期!
然而,在另一项III期临床试验NeoTRIPaPDL1研究中,新辅助化疗(白蛋白紫杉醇联合卡铂)的基础上加入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却未能显著提高TNBC患者的pCR率,且与PD-L1的表达状态无关,EFS数据有待进一步随访[26]。与KEYNOTE-522研究相比,我们深入分析NeoTRIPaPDL1研究获得阴性结果的可能原因如下:①、两者入组人群的疾病分期差异较大(KEYNOTE-522研究纳入的患者临床分期更早,可能有更高的免疫浸润);②、两者样本量及PD-L1阳性比不同(KEYNOTE-522研究样本量更大且患者PD-L1阳性比高达82.7%,NeoTRIPaPDL1研究中仅为56%);③、两者新辅助化疗方案不同(KEYNOTE-522研究为卡铂联合紫衫序贯蒽环;NeoTRIPaPDL1研究为卡铂联合白蛋白紫杉醇);④、两者药物机制不同,两项研究分别选用PD-1抑制剂与PD-L1抑制剂,两种免疫治疗模式或在机体中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同样获得阴性结果的还有GeparNuevo(GBG 89)研究[27]:这项II期临床研究中的eTNBC患者在随机后分别在窗口期接受2周的度伐利尤单抗或安慰剂治疗,随后继续予以度伐利尤单抗/安慰剂联合化疗(白蛋白紫杉醇序贯表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新辅助治疗。结果显示,尽管度伐利尤单抗组(53.4%)PCR率虽高于安慰剂组(44.2%),但未见统计学差异(P=0.287);然而,在2周窗口期接受度伐利尤单抗治疗的患者pCR率有获益趋势(61% VS 41.4%,P=0.052),提示窗口期给予免疫治疗的方式有望提高eTNBC患者的PCR率,后续正在进行的III期GeparTreize(GBG 99)研究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20年IMpassion031研究结果重磅出炉,力证阿替利珠单抗在eTNBC新辅助治疗中的优势,无疑给免疫治疗的新辅助地位再次打入一针“强心剂”:该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的Ⅲ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白蛋白紫杉醇序贯多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在早期TNBC新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ITT人群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组较对照组pCR率提高了16.5%(57.6% VS 41.1%,P=0.0044),PD-L1阳性患者与ITT人群pCR获益一致(68.8% vs 49.3%,P=0.021);即使是PD-L1阴性患者,其pCR率仍然有获益的趋势(47.7% vs 34.4%)[28]。然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同样是阿替利珠单抗,在IMpassion031研究和NeoTRIPaPDL1研究中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究其原因可能与两者入组人群病理特征、PD-L1检测手段以及化疗配伍方案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因此更凸显免疫治疗在TNBC中需要个体化、精准化用药才能使疗效达到最大化。总而言之,KEYNOTE-522研究和IMpassion 031研究均证实了PD-1/PD-L1抑制剂在TNBC新辅助治疗中的重要价值。
三、eTNBC与PD-1/PD-L1抑制剂辅助治疗
目前已报道的PD-1/PD-L1抑制剂在eTNBC辅助治疗领域的研究结果有限:帕博利珠单抗的作用在KEYNOTE-522研究中已得到初步验证,而阿替利珠单抗在IMpassion031研究中的生存数据并不成熟。此外,辅助治疗领域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还包括SWOG S1418/NRG BR006研究、IMpassion030研究、GBG 99研究等,也期待这些研究未来在这一领域给予我们更多的临床提示。
四、TNBC免疫治疗的未来方向
尽管免疫治疗在TNBC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些许成绩,但仍旧缺少行之有效的临床标志物来筛选出TNBC免疫治疗的潜在优势获益人群,而这也将成为乳腺科/肿瘤科医生治疗TNBC患者纠结是否选用免疫治疗的最大根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海复旦肿瘤医院邵志敏团队已走在前列:他们在2019年发表于《Cancer Cell》的研究总结提出了我们国人的TNBC四分型[29],即管腔雄激素受体亚型、免疫调节亚型、基底样免疫抑制亚型、间质样亚型,这也是首次基于国人基因特点的TNBC分型;而他们在随后的FUTURE研究中纳入了69例临床难治型TNBC患者,其中19例患者被归类为免疫调节亚型,在临床治疗中则根据此分型特异性的给予白蛋白紫杉醇联合PD-1抑制剂治疗,其ORR率高达52.6%[30],明显高于既往mTNBC中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ORR数据,充分说明TNBC免疫治疗不能一概而论,需做到个体化研判。笔者团队也在前期研究中尝试探索这一问题:我们在TNBC微环境间质成分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中发现了一种新型、独立作用的雌激素受体(G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的表达,它可介导CAFs发生葡萄糖及谷氨酰胺代谢重塑,这种微环境的代谢改变会诱导TNBC细胞中PD-L1的表达增加并损伤CD8+T细胞的细胞毒杀伤功能从而使肿瘤发生免疫逃逸与免疫治疗耐药;同时,临床间质GPER阳性表达的患者其接受PD-1/PD-L1免疫解救治疗的PFS时间显著减少[31-35],我们的数据提示TNBC中间质GPER的表达状态或可预测mTNBC患者临床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有望成为筛选免疫治疗优势获益人群的潜在分子标记物,但这一假设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体内及前瞻性临床研究来证实。
综上,笔者坚信未来TNBC免疫治疗的研究方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探究不同免疫疗法的联合及免疫疗法与传统治疗模式的选择,评估联合治疗的最佳时机、先后顺序以及联合治疗的效果,从而达到优化患者的治疗,进而延长患者的生存;②、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免疫治疗的疗效,对于免疫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怎样更好地把控,提高临床免疫治疗的安全性等问题;③、构建临床PD-L1检测的高效、同质化体系,且应当是从抗体到检测平台及判读等一套完整的体系,缺一不可;④、在生物信息学、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与AI人工智能辅助等技术参与下,从基因水平探索TNBC不同亚型相关的肿瘤免疫驱动因子,实现不同亚型、不同分期的TNBC患者个体化、精准化免疫治疗。
五、总结
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开创了TNBC治疗的新纪元,我们对此寄予厚望,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TNBC免疫治疗的道路上必将充满着挑战,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面临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越来越多的TNBC患者将从免疫治疗中获益,而TNBC的个体化、精准化免疫治疗时代终将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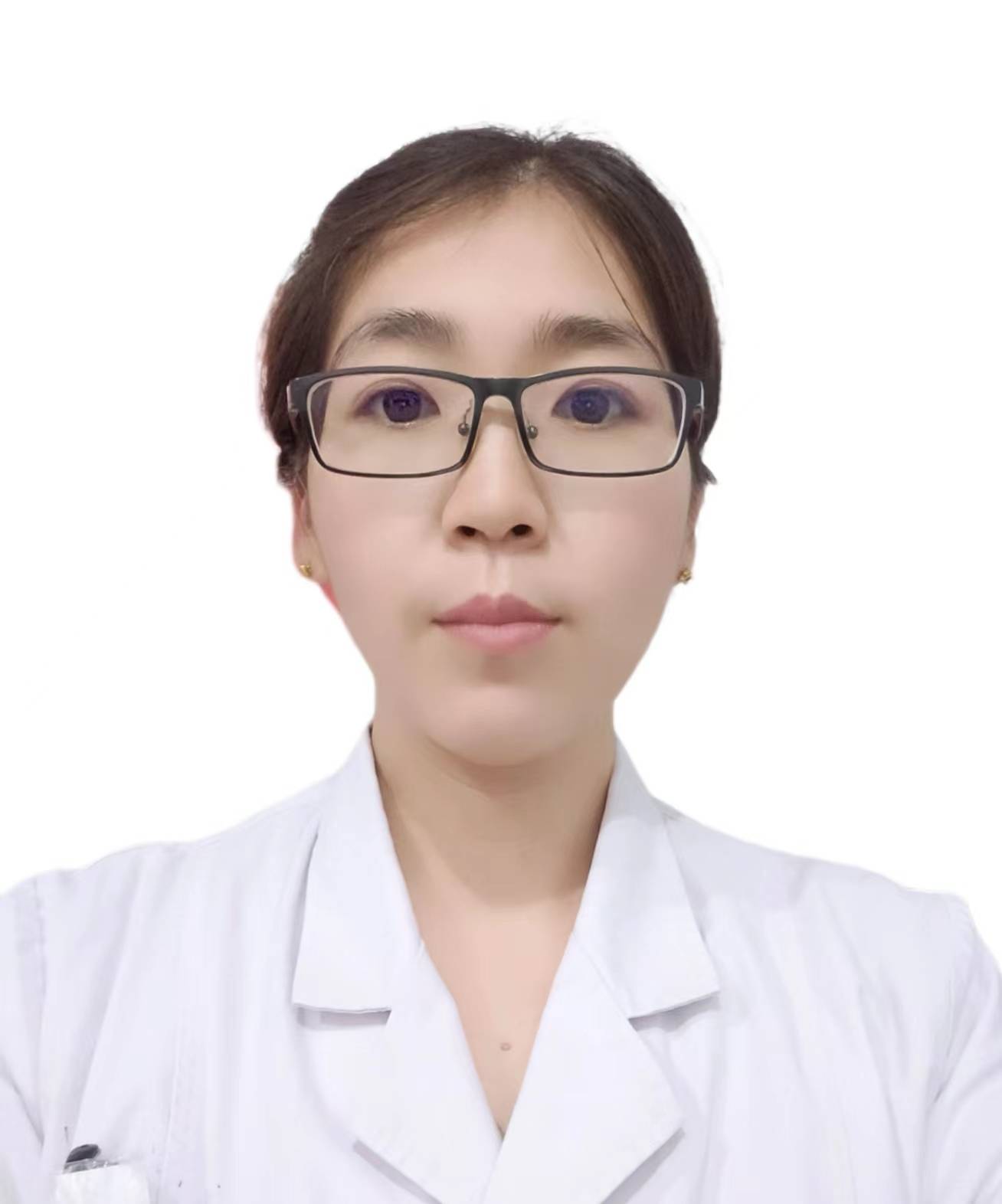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苏公网安备32059002004080号


